「一個穿著風衣、手拿塑料袋、外表謙和的亞洲人走了進來。這是“紐約無成本制片之王”特德·霍普(Ted Hope)描述第一次見到李安的情景。在此之前,霍普因為看過李安畢業作品《分界線》,而注意到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而李安經過朋友介紹,來見這位“紐約唯一一個可以用非常低的預算把電影做好的人”。于是很自然地就發生了開頭的這段對話。這次見面,開啟了霍普與李安的合作之路。霍普作為制片人與李安合作了早期幾部作品,他發掘并親身見證了這位當代杰出導演的冉冉升起!今天讓我們聽聽霍普講述世紀之交的紐約電影圈,尚未成名的李安是什么樣的,“李安電影”工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幕后故事!本文摘選自特德·霍普著作《希望為電影:從“紐約無成本制片之王”到產業革新先鋒》(已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這看似是一句無關痛癢的話。但對于好機器公司合作過的最賺錢、最受尊敬的導演李安來說,這可不只是一句提出要思考一下的無心之語。因為李安真的會花一分鐘去思考一下,甚至比一分鐘久得多。可能你和他說了什么事,他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后你就去忙別的事,比如吃了個午飯,再接著做別的事了。這時,李安會來回答你幾個小時之前問他的問題,而他自己常常不覺得時間已經過去了,或是期間已經發生了其他事情。他就像是仍在之前那個時刻那樣,同樣還要求你也回到提問的那個時刻。于是我們明白要給李安充分的時間,因為他常常會因此提出一些重要的或者絕妙的點子。在他拍攝早期的電影《推手》和《喜宴》時,助理導演或是其他劇組成員會憂慮地跑來對我說:“李安又進入那種狀態了。”于是,我會向片場望去,看到的往往是李安一動不動、皺著眉頭,或若有所思的樣子。他正在思考,許多同事則站在一旁盯著他看。我們在拍電影的時候很容易陷入一種慣性思維,以為每個導演都會遵循某種固定的工作方式。這種“一刀切”的思想正在腐蝕電影制作。但李安讓我意識到,如同每個工作人員、每個演員那樣,每個導演都是獨特的,都有著自己的步調、風格和洞察力。而制片人的(其實也是所有合作伙伴的)任務是了解并保護這個導演獨特的工作方式。這里沒有規律可循,只能以這種原則為中心,為導演量身定做制片方式。對于李安來說,他的一些特點可能來源于他的文化背景。他出生于臺灣,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才搬來美國就讀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而后又在紐約大學帝勢藝術學院繼續深造。但是,光看成長背景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考慮到每個人作為個體的獨特性。我在紐約大學讀書的時候有幸看過李安的畢業作品《分界線》( Fine Line )。我認為這是紐約大學出品的最好的短片之一。短片的主演是查茲·帕爾明特瑞( Chazz Palminteri ),這是他出演的第一個角色。短片講述了一個小意大利的高加索男孩和一個唐人街女孩的愛情故事。影片采用手持攝影,生動真摯。早在那時,李安就已經清楚地知道如何用鏡頭捕捉情緒。但我對他一無所知。我甚至以為他是個意大利人,因為他(和馬丁·斯科塞斯一樣)上的是紐約大學,而且他影片的背景是在小意大利。我還認為他的名字一定是個藝名,一個名叫“安格爾 - 伊”(Angle-E)的美籍意大利人。那是一個充斥著涂鴉和標簽的時代。我就是喜歡瞎猜,能怎么辦呢。在我剛開始做制片人的時候,我曾經列過一個想要合作的導演名單,上面有李安、妮科爾·霍洛芬瑟(Nicole Holofcener)、凱莉·賴卡特(Kelly Reichardt)、菲爾·莫里森(Phil Morrison)和馬克·弗里德伯格(Mark Friedberg ),他后來成了一名優秀的美術總監,參與了許多部李安的電影)。后來,當我真正開始去找導演時,李安就是我找的第一個人。而且,當我向詹姆斯·沙姆斯那樣的潛在合作伙伴闡述道想要創立一個制片人主導、導演驅動的電影公司時,我總會想到李安。萬事俱備,只差找到李安了——但我沒有聯系到他。我翻遍了紐約電話黃頁(那時還沒有網絡),我也給他的經紀人打過電話,但他并沒有與我合作的打算。直到李安來找我了。一切真是太巧了。那是在 1990 年,要不是我放棄去圣丹斯電影節,我可能永遠都不會認識李安。那年,詹姆斯擔任了托德·海因斯( Todd Haynes )《毒藥》( Poison )一片的行政制片人( executive producer ),而我則當了哈爾·哈特利《信任》( Trust )一片的執行制片人。由于當時還沒有會計軟件,所以必須有人留下來清算賬務。而圣丹斯在那時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電影節。于是,我想:“我去電影節干嘛?還是個遠在猶他州的電影節。我可是個制片人。”于是,我坐在特里貝克一個混亂的街區(沒錯,特里貝克也有過混亂的街區)中,一家叫“紐約娃娃”的脫衣舞夜總會樓上的小辦公室里,清算公司第一年的賬務。然后,一個穿著風衣,手拿塑料袋,外表謙和的亞洲人走了進來。他說道:“打擾了。”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為什么會來。他接著說:“我是李安。再不拍電影我就要死了。”他把袋子放在我桌上。里面有兩部劇本,《推手》和《喜宴》。這兩個劇本都參加了一個臺灣地區的劇本比賽,并贏得了獎金。我倆共同的朋友大衛·拉瑟森( David Lasserson )告訴他,我是紐約唯一一個可以用這么低的預算把電影做好的人。有錢拍一部電影并且知道會有更多的錢來拍下一部電影可謂是一件幸事。但光有這些仍不足以把事情做好。我們需要想方設法節省開支。李安非常急切地想要拍電影,所以為了完成他的電影他在所不惜。如果他只能籌到這點錢的話,他一定會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一開始合作,我就明顯地感覺到,就算有了正確的態度,要和李安一起拍片并不那么容易。他有自己風格上、文化上、個性上獨特的行為方式。我們用 35mm 膠片,花了 18 天時間拍完了李安的第一部電影《推手》,總成本大約為 35 萬美元。在這之中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長,而且一天比一天漫長。由于當時工會和眾制片廠有爭執,所以紐約的電影工作者們都沒有工作可做。因此,我們劇組的每個人都因為能有事可做感到非常高興。由于《推手》中有一部分是中文的,人們都覺得這部影片不會成什么氣候。那時候,美國電影,尤其是獨立電影都沒法在圣丹斯賣上幾百萬美元,也不太可能會有什么海外的影響力。所以,這部電影對劇組的人來說只是讓他們能有個工作罷了,其他一無是處。人們只是來工作,僅此而已。但由于預算實在太低,我仍然覺得我們的資金就像是消失在時間的縫隙中了一樣。我必須要更合理、更高效地完成制作。我們常常因為拿不定主意而浪費資源。在制作低成本影片的時候,你通常沒有時間思考,每秒鐘都在行動,都在解決問題。我們本應該超前考慮問題,但實際上卻頻頻落后。從我制片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換掉當時的助理導演,不仔細規劃每場日戲和夜戲,我們絕對無法按期完成拍攝。由于想和做之間常常有一段要命的距離,所以我想了幾天才開始行動。我在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后,終于決定換掉助理導演,列出了制作日程并要求執行。對,我們要來真的了。由于我們的資金已經不夠再找一個助理導演了,于是我干脆就當起了助理導演。事情開始起了變化。如果李安想要完成電影拍攝,劇組必須要遵照嚴格的指令,因此能有一個權威的領導在片場坐鎮對他來說再好不過了。每天開工前我們都要過一遍分鏡表和拍攝計劃,每天收工后都要過一遍第二天的計劃,在拍攝過程中也需要常常重復這樣的工作。我們還需要常常告訴李安現在的拍攝進度是提前了還是落后了,然后接下去要怎么做。如果我們沒法讓李安和攝影指導拿定主意,或是偏離拍攝計劃,影片的制作就容易擱淺;但如果他們都能果斷決策,我們就能飛速完成任務。劇組成員都會響應果斷的決策。但到后來,他們習慣于總是響應決策了。(諷刺的是,我覺得可能因為他的前兩部電影制作得過于嚴格,李安在之后的電影中總是希望能有更多靈活的、即興的創作。)那段時間,我和李安私交甚密。那是因為,由于電影的制作經費很緊張,我不僅要擔任制片人和助理導演,同時還是李安的司機。我會載著他在往返片場和他位于白原鎮的家之間的路上討論拍攝計劃。但在每天工作了 15 小時之后,你已經很難專注地開車了,這個導演也已經累到常常忘了自己家在哪。我以為我已經清楚去他家的路,但一次次的,我們不是開過了,轉錯彎了,就是下高速的時候下錯出口了。很多時候,我們已經離那個該轉彎的路口兩三千米了,李安才突然想到說:“嘿,你錯過那個路口了!”——這句話對許多電影制片人來說是個很恰當的比喻(“錯過路口”:miss the turn ,亦可以指“錯失機會”)。「李安:我不是很溫柔的人,我覺得做人可以很溫柔很中庸,做藝術不能手軟。我喜歡像鵝的脖子一樣,很圓潤,但是底下折了三折,這樣我覺得比較安心和對得起觀眾。」李安從紐約大學畢業后的六年間,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里寫作、做飯和帶孩子。眾所周知,李安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這一點從他拍的短片就能看出來。但是,因為他不是那種善于向大人物推銷自己的人,他的成就與他的能力并不相當。所以,從他拍完第一部長片到第四部長片《理智與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的這段時間里,他住的那棟公寓里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鄰居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導演之一。在完成《冰風暴》之后,我們都勸李安搬家,給他的家人找個像樣的房子住(他后來終于這樣做了)。畢竟,那時候他已經賺了不少錢了。你可能會將李安的原地不動理解成奇怪的行為,但他其實只是極度專注在他的工作上而已。當你看到李安的時候,你可能常常會想,他是不是又在“花時間想事情”了。他可能確實花了好多時間來思考,但他絕不會做出輕率的決定。李安有一個獨特的本領,就是他似乎能在拍攝的時候看到整部電影,并在腦海中緊緊地把控整部影片:如何將鏡頭組合在一起并讓它們相互呼應;如何用場景來營造觀眾的期待;如何發展人物等。當你腦海中充滿了創造一整個世界時會遇到的難題時,你幾乎無法思考其他事情。而且對于李安來說,他似乎并不只是在思考他手頭正在拍攝的這部電影,他還會考慮當前的工作對于他要創造的下一個世界會有什么樣的幫助。所以說,如果他錯過了幾個路口,或是在原地比別人站得更久,一點也不奇怪。許多人都在那時候學會了要換個角度思考。如果制片人的任務之一是激勵導演去實現他們的夢想,去追尋人人支持的愿景,那任務之二就是把夢想拉回現實,讓導演了解到用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可以達到怎樣的效果。制片人的第三個任務是幫助導演認識到:這些不足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李安在拍攝他的早期作品的時候就已經了解到各種各樣的不足是如何對拍攝產生積極影響的了。他因此非常明確完成一部電影所需要的時間和怎樣有效地利用這個時間。他也非常清楚什么時候可以停下來思考問題,來確保能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下去。在李安聲名鵲起之前,我常常需要去找那些能接受李安的人來合作。但這著實不太容易。李安是一個溫和的好人,但他常常讓人難以捉摸,有時還會嚴格要求別人來給出他要的東西。我需要找到那些不會被這一點嚇跑,也不會將李安不直接和你交流誤解為他沒有意見的人。美國人通常希望領導者決策果斷,而我覺得電影圈似乎對不符合這一點的人存在偏見。放到片場上來說,這種偏見常常會對非美籍導演或者女導演不利,因為他們的行事風格不同。但我們需要學會接受不同的領導風格,否則我們很可能會失去與許多出色的藝術家共事和碰撞的機會。但有時,我們卻好像在說不同的語言。在拍李安的第二部電影《喜宴》時,我們給年輕的女主角挑完衣服,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但李安卻示意停下來。當時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好開拍了——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那天,我們要拍的是金素梅的戲。當她穿著我們挑選的服裝出現時,李安一臉痛苦的樣子。我得弄清楚為什么。就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過來,李安從來不會站出來表示自己不喜歡什么東西。所以,給李安制作電影首先要學會怎么問他問題,比如“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嗎?”光問“你喜歡這個鏡頭嗎?”是不夠的。你得問他“我們要不要再拍一條?”你得琢磨出怎么問他才管用。這么一來,李安也習慣了這種拍出“李安電影”的工作方式了。我和《臥虎藏龍》、《綠巨人浩克》( The Hulk )、《斷背山》( Brokeback Mountain )的劇組成員談過這個問題,許多人向我反映過類似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在制作期間仍然存在,幾乎在整個后期制作階段都會出現。李安會說:“要有些羊從山上來。”人們會回答他說:“為什么?現在的這些羊有什么問題嗎?你是不是要多加幾只羊?”“對,”問了他一大堆問題后,他終于回答說,“我想要再加幾只羊。”每個人都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方法。制片人常常需要想辦法讓大家達成共識:找到人人同意的可行方法。許多導演都跟我講過他們妥協的過程:通常一開始只是一個較為公平的妥協,但到后來就發展成了一系列的妥協,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協,到最后甚至已經遠遠背離了他們進入電影行業的初衷(這樣的妥協過程常常是他們在和好萊塢制作班底合作時所“害怕”的)。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文/特德·霍普 來源/拍電影網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pDEMcNDfxAbD78pBN78w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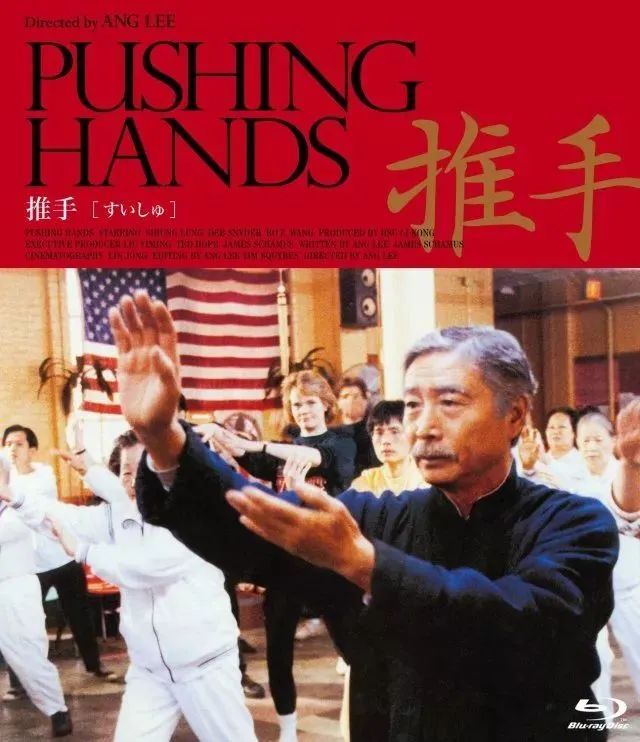






表情
添加圖片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