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電影有著超群的魔力,能使我們感同身受產生共鳴,然而電影本身,卻很難定義。那些將我們和生活聯系起來的短暫線索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在我們面前成為現實,最后沉淀于記憶深處,愈是想要清晰刻畫電影的本質,卻愈是加固了達至本質的屏障。未知就像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亦在其影像中呈現,因為如果電影的核心是某種物質性的東西,那么他的靈魂究竟會包括什么?

(電影是一種語言,他可以描述東西,抽象而龐大,一些人是詩人,擅長用優美的字句刻畫事物,但電影語言是獨一無二的,你可以表達無法用其他方式傳達的感覺和想法)電影可以將你腦海中的畫面變成現實,但無論是哪種電影之美,在其如變戲法般出現之前一個電影畫面仍然只是一個想法,它從電影導演細微的生活經驗中誕生,但只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意示著什么,而如果我們要打破電影敘事空間和現實之間的屏障或者最終可以留給我們的是一場對話,我們與那些對世界持有獨特看法的人的對話,也許還真是那么回事(沒有其他,只剩攝影機,那些美妙的人兒就在黑暗之中)

這就是電影的本質,共同的想法跨越人群和時間,成為我們共享的經驗,在這方面,電影比其他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超出如此之多,因為它自身具有一種普遍性,而這種凝聚力就是電影的靈魂所在,幾乎所有藝術都能看作是一種敘事活動,雖然藝術依其內在本性,都能被如此歸類,但每種藝術形式各有不同作法,電影在各種藝術形式中,顯得最為包容,因其內在本性,就是為卓越杰出的故事服務,藝術媒介若要獲得矚目或超越極限,就需將自身極致發揮,例如,雕像定格了某一個瞬間,雖然它可以從不同視角觀看,我們所見的依然是由物質性限制的素材所制成的雕像而已,電影通過這些局限性要喚醒的除了人的外在形態,還有更多。它在藝術中稱得上是一支獨秀,因為它的元素,視覺素材,暫時的線性特征,再配以電影對時間的操控,意味著對作品的每一處體驗,都是流逝中的時間,無論是在作品本身,還是在觀者的眼中,皆是如此。
若強調敘事線性,就會讓時間的流逝變成一場災難,我們都在見證一個時刻,這一時刻無法復制,而由此引起的緊迫感升華為藝術家對永恒的認識,縈繞于藝術家的心頭,而這種永恒與人類的有限生命相對立。

這與效果逼真的視覺元素相輔相成,而其他藝術像是卻沒有如此的復現能力,但于電影而言,卻可以說是其一大特色,它對敘事的內在要求來源于電影導演與這種自我意識的對抗,不僅僅是作為藝術家,更是作為人(這也就是為什么比較差的導演,某種程度上他們最大的恐懼是自命不凡,所以一方面你真的想做點什么成就,另一方面你又不允許自命不凡,有趣的是你說滾蛋,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自命不凡或者是我做沒做,我知道的就是去看這個)
電影伴隨我們成長,它可能是藝術形式自我反思的巔峰,帶有一種無法避免的天性,電影深深觸動了許多人,也許是因為電影是人類歷史上所有故事的藝術巔峰,而視頻拍攝和電影也許正意味著豐富人類生活本身的故事。

如果我們要給予電影一個靈魂,那我們一定要把電影想象成整體性的存在,將媒介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而不應忽視任何一個方面,所以當談到電影的本質時,沒有哪一部分會被忽略。
電影就是響尾蛇,為了生存,他會吞下前面出現的一切,在電影早期,個體主義進路的種子是由最先鋒的導演種下的,藝術家學習電影語法教條的時候,他們對電影的假定還是很簡單的,電影由其他藝術語言構成,基于傳統的表達方式,但又需要增添某些印象主義手法,避免將電影置于過于抽象的層次,而是將個人的世界觀注入電影。僅僅是幾十年之后,兼顧電影戲劇性和風格性的個體主義路線開始付諸實踐,作者論誕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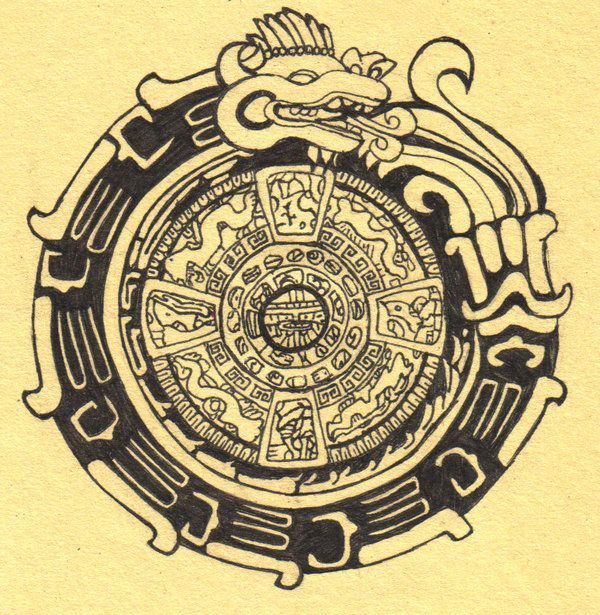
關于作者論的討論至今在延續,誰是作者,誰來規定誰是作者,此類的爭論仍是亂成一團,我們傾向于相信作者就是能被一眼認出的電影導演,某些典型特征在他們的作品中反復出現,這點無容置疑,但這樣來辨別作者也是最膚淺的,是的,在安德森喜歡強調各種裝飾物同時,尼古拉斯溫丁也會用霓虹光和極端的布光來裝點他的電影,但這會是將“作者”的意義局限在視覺的領域,忽略了電影的真正本質,最偉大的作者不僅能創造出最好的影像,還能夠用這種形式來傳達最具遠見和顛覆性的理念,有人可能通過對創作者進行心理分析,以洞察電影的靈魂所在,電影的本質根植于理念,而這些理念源自于人,但正是這種個體主義方法,鑄造了電影的靈魂,每一個特寫,每一次攝影機啟動,每一刻沉默,這些不能僅僅看作是電影的視覺語言,因為必須要領悟這種“語言”的弦外之音才能發現其深意,而此深意只有電影才能給予我們,因為如果一幅畫面是一個理念,那么電影畫面構成的序列就是復雜理念的呈現,每個藝術家為了能夠更全面地表達自己,他們必然要找到最好的表達方式來傳達他們在鏡頭背后想要的一切,內在含義往往從導演自身個性與素材的張力之間溢出,《電影手冊》稱頌那些能夠運用電影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的導演,稱頌他們創造出了傳達內心渴望的新方式,最終現代主義與電影融合,它從其他藝術中提煉出了自己的氣質,并很快意識到,鏡頭可以將電影自己變成重要主角。

并不是說電影在過去沒有自我指涉,如吉加 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 但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節點,作者論可付諸于電影制作實踐并更好地探索電影作者們的個體性,希區柯克真的將自己拍進電影,參與到稱之為“集體性個體主義”的一場電影運動當中。
電影以某種方式實現了這一理念(集體性個體主義)卻因其只是集體性的電影故事整體中的一部分而大受限制,它存在是因為有先行者的鋪墊,以及對后來者的促進這種本質特征無可避免,有些人覺得它是陷入了困境,也有人覺得這可以用來操縱,觀眾對藝術形式的期待,因為電影看上去有討論自身的內在需要,這最好是從電影導演而非觀眾的視角來理解。
想象一下你自己有能力和資格用抽象的手法盡情表達心中所想,那么,哪怕只是意識到自己作品中的缺陷,我相信即便是對電影的嘲諷,也無異于對他的贊頌你推舉你之所愛,也認識到它之弊端所在。

有時候,電影的本質性問題,有賴于那些不斷追尋電影內在邏輯的人來解決(畫面和聲音本身什么都不是,他們所呈現的意義只存在于,他們融合轉化而成的東西上)
這讓我想起我認為電影里,最好的關于自我探索的例子。在《八部半》中,費里尼將之作為作者論的實踐,探索自己的過去和現在,表達他的暢想,巧合的是,電影中所有的視角都來自一名電影導演,他在絞盡腦汁思考下一部電影該怎么拍,關于《八部半》有個事實,那就是沒有人能只需要觀看一邊就能理解,因為受人尊重的世界級導演在江郎才盡之后所發生的事情,使得他最終實際上拍攝了一部關于自己的電影,關于失去電影導演能力的自己,于是成就了《八部半》,我認為《八部半》完美的囊括了電影的靈魂所應該包含的一切,他的開場如夢似幻導演在云中漂浮,另一個角色用繩索將他拉回現實,事實上,我們在這個畫面中看到的,是費里尼的真實想法,這電影從頭到尾所講述的是費里尼想要借助電影的視頻拍攝過程來更好的了解自己,但同時他又不得不將這部作品完成,如前所述,他正在經歷時間的流逝,電影一直以來都在時間中經歷自身的變革,它是合二為一的嘗試,他想創造自己的代表作,卻一直處于藝術破產的狀態,一個騙子欺騙別人相信他的藝術天賦,但他卻不知道自己該怎么做,《八部半》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看待電影和導演的角色,因為費里尼在最后認同正是那未知的想法定義了藝術家,他完全接受了電影的模糊性,因為這正是電影獲得超群魔力的原因,我們會被電影凝聚在一起,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并不知曉其中意味著什么,有人可以在明天創造出完全顛覆我們先見的東西若這是真的,電影一旦拍出這就會發生,費里尼聲稱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怎么實現,但電影證明了,其實他知道得很清楚,在這樣的視域下,最為精彩不過的是,在他盡皆荒誕的作品里來一場和諧共舞的狂歡慶典,結尾處所一場慶祝導演接受自我的狂歡省盛典,因為在等級社會里人們無論處在什么地位,都可以用電影這個媒介將彼此綁在一條船上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只知道他將帶我們到某處。費里尼頹廢的導演風格以及自我沉溺的敘事方式比起任何被同質化的好萊塢電影都更令人向往。

我們希望電影能給予我們與眾不同且惟電影所獨有的東西,現在我們對電影理解達致了多深處?我們觸及到皮毛了嗎?不,沒有,電影沒有皮毛,電影是對我們生活的抽象,一個模仿另一個,它與我們共同成長,我們贊賞它,是因為電影給了我們做夢的能力,讓我們能在轉瞬間看到人類潛能的完全釋放,電影之所已存在皆有賴于人類的潛能,它是我們做過的每一個夢,每個人惟其能感受的故事,投射并在人群中產生回響,電影的靈魂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共享,我們與電影的共同之處就是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我們都不確定自身在人世間的位置,但如果我們去探索或許會有人靈光一閃并薪火相傳,長此以往就會有人意識到電影的表達力量,我們可以見到,電影擔任著促進人類進化的重任,因為觀看電影就是觀看每一個曾經活過的人的想法和夢,就是與每一個尚未出生的人進行對話,如果電影的靈魂不是這樣,那還能是什么呢?
內容由作者原創,轉載請注明來源,附以原文鏈接
http://www.jgug.cn/news/3747.html全部評論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表情
添加圖片
發表評論